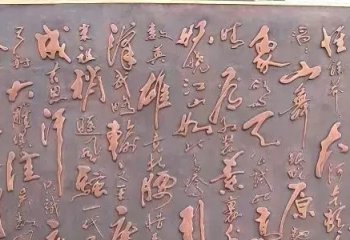看了“鄒建平、劉鳴當代水墨藝術探索研討會”的文字實錄。參與研討的人員近30人。批評家涉及老中青三代。看后,作了一些分析:首先發言的是鄧平祥,鄧老師從西方繪畫和中國水墨的長處出發,夸獎藝術家的結合“擴展了水墨的表現力”。鄧老師的批評風格還體現在:把一件藝術作品進行支解,分為若干部分,然后打鉤評分。他說:“在語言上有兩個層面,我認為一個是語言結構,語言結構是最難的,還有一個就是構成的結構,我感覺鄒建平的繪畫是兩種,不斷解決了語言結構的問題,也解決了構成結構的問題。

“試問:“有”就變成了好!鄧老師是口袋里邊揣著藝術進步論和藝術史需要填補空白的觀念來進行評價,這種評判的結果因為其評判標準的寬泛性必然導致結論的偏頗。陳孝信則走向了與鄧平祥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將參展的兩位藝術家的作品進行比較,試圖找出他們之間的差異。對于藝術家的共同點,他所使用的詞語如下:“精神性的追求“、“重視墨和光”,從而最終得出了兩個人是有差異的結論。

事實上,這些表揚的詞語中并沒有多少個詞指向實質意義。陳老師所強調的“現代水墨不屬于中國畫“、“現代水墨藝術屬于當代藝術”并沒有在具體到談及藝術家作品的時候給出明確的劃分。我認為既在界里也在界外,也不能細說界里比界外更加成功。這些模糊和模棱兩可的和玄拗的詞語構成陳孝信的敘事邏輯。皮道堅的發言像黨小組的組長,他對藝術家“善于利用各種各樣的資源“做出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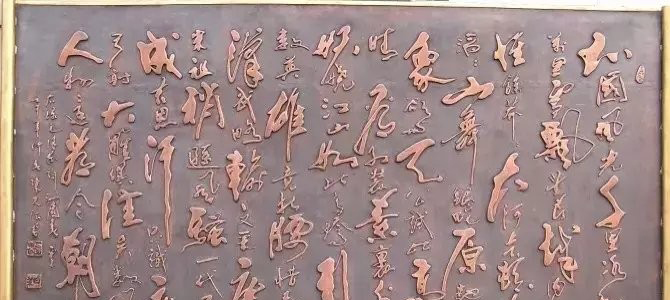
他的發言大有對這兩位舉辦展覽的藝術家、為這個展覽以及為多年來“推進了水墨畫的國際化進程“的批評家們表示由衷感謝的意思。旨意很明白:“我”是有“眼光和眼界的!”。話到這里就戛然而止了。那么“您”的觀點是什么呢?

賈方舟的發言先對展覽的“標題”做出闡釋,肯定了藝術家的思考與標題的吻合。然后,就對藝術家作品的寓言性和象征意義進行解讀,把藝術視為“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文化類型的一種思考和回應”。在他的發言中,將水墨藝術換為當代藝術,或者雕塑作品,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賈老師在這段發言中因為缺少實質和針對性,必然會導致“觀念圖解”的撞車和悲劇。

王林的發言也具有賈老師的特點,他對于水墨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語言特質避而不談:“最讓我有感覺的地方是他們繪畫中所表現的那種矛盾和沖突,“、“還有中間的暴光,被最近稱為“母體”,我認為是畫面上非常能夠抓住人的地方。“徐虹的發言:“因為前期男女之間出現在畫面不同身份和性別的那種關系,使我覺得他還有更豐富的含義…“徐虹更多的是對藝術家作品的想象以及觀念的演繹,這些過于飄逸和抒情的句子,不知道是否能夠貼近藝術家的心?鄒躍進從理論上進行解讀,同樣偏離了作為藝術主體的畫面語言,滑入到“一千個哈姆雷特”的身份。
確實“鄒躍進先生。他從頹廢的角度對鄒建平的《槍女郎》進行了解讀,又對劉鳴先生的新作進行了解讀,讓人很受啟發。“但是幼兒園的學生作品與藝術家的作品區別在哪里呢?觀眾不缺乏想象能力,他們缺乏的是對作品好在哪里的鑒別能力。鄭林則面對已經“躍然紙上”的作品,卻談論如何去畫畫的問題:“怎么做作品,怎么解決傳統和當代性的東西。
我們從油畫、從裝置,實際上也可以發現很多問題。都存在一個內容觀念和形式的問題。我覺得一個藝術家不解決這些問題的話,最后還是沒有解決根本性問題。“這種談話必定是錯位的。理論再多也沒法把作品說出來。如果這樣的談話帶有對藝術家作品不甚滿意的意思,那么就應該說出不對在哪!在諸多參與發言的批評家中,只有廖少華、余丁、呂澎、王小箭、楊衛、吳鴻的發言顯現出了更多的可取之處。廖少華、余丁的發言圍繞藝術家無法拋開“手藝活“的本質來談論“傳統藝術的當代性”。
強調了那些別人不可復制的“絕招“才是藝術家相互之間進行PK的利器;呂澎在談話中對水墨藝術家的“身份焦慮”進行化解,他在劃定好的作品是展現“中國氣質”,而一般的作品則是符合個人的真實性的時候,他作出了判斷:“鄒建平的作品從80年代到今天,而且也符合這個人對藝術理解的某種真實性。相對而言劉鳴的作品,更文氣的東西并不是說作品上面有沒有出現現代語言這些東西,那倒不一定。
“他所強調的藝術沒有主流和非主流的說法,這些都是為藝術家的后顧之憂鏟平道路。王小箭、楊衛、吳鴻在發言中體現了他們對畫面極強的把握能力,王小箭從作品所傳達的效果,和藝術家對姿態刻劃得比較到位的判斷之后,得出了進入女性主義角度和人文主義角度解讀的可能性。
他的表述比劉虹和鄒躍進有公信度。楊衛從藝術家的作品對光的運用中找到中國當代水墨畫都是“經過了全球化”洗禮的依據;吳鴻的敘事邏輯值得稱道。他從藝術語種的區別出發,談到當代水墨創作的語境,然后具體的解讀兩人的作品中。他從藝術家作品表現的是夜景中找到“光”的必要性。對作品來源于長沙夜生活、以及與飲料與酒的勾兌所包含的象征意義作出理解,細心審視了藝術家的生活觀察與體驗等。
盡管其從女性和槍支的畫面中,引申到了雅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系顯得有點牽強。這些都有助于豐富藝術家作品的文化內涵。但他們同樣所欠缺或者說回避了“藝術家的身份在哪里?”的價值判斷,是“問題重于作品本身”的贊同者。“鄒建平和劉鳴是湖南非常優秀的兩位畫家。
“這一句話就是由畫家朱訓德說出來的。這是他評價這兩位藝術家第一句開場。這里邊涉及到了對藝術家藝術成就的評價,對藝術家作品作出明確的界定。這是引起觀眾去了解一位藝術家的原始欲望的構成因素。當然,發言的批評家都有機會說這樣的話。但是沒有人這樣進行評價,當“優秀”這個詞需要實起來的時候,這種評價確實有難度。就整個討論會而言,畫家的發言要比批評家顯得實在和誠懇。
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并不缺乏批評的眼光,比如:畫家左漢中在發言提到,“他們的作品畫得比較黑,用墨很重。其實水墨畫畫得很黑很難把握,弄不好會產生污濁之氣,但是他們兩位都很能駕馭墨色,敢用重墨。可以說絕大部分的作品,是擺脫了那種晦暗之氣,為了打破重墨的呆板和不透氣,都采用了一招用‘光’“。這是讓我第一次對兩位藝術家的作品除了主題之外,關于形象或者說畫面效果的第一次想象。
陳湘波從畫面給人的感覺,而不是觀念給人提供的感覺作出評價:“劉鳴在他的這次展覽中,第一次看到他的水墨畫和裝置相結合,也試圖通過不同的形式做一些突破,做一些當代的表現。但是中間有時候會不會覺得還是有點生硬;而劉鳴對筆性、對水跟墨和宣紙的把握有一種很天然,但是怎么樣跟當代的生活結合,這個點能夠把握得更準。李小斌對批評家們對鄒建平花鳥畫的集體失語作出補充:“我覺得建平的東西,很多人都在關注他的人物,實際上他的花鳥,還沒有作為一個話題,非常好,甚至在某種語言表述上,我覺得比他的人物要更加精致一些,這是作為一個畫畫的人的一個感受。
“這又是對批評家們的一個諷刺,因為“花鳥,無觀念”,所以大家失語了!多數的藝術家能夠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對觀念問題則點到為止,這與多數的批評家發言構成鮮明對比。盡管多數畫家以及畫家發言中也暴露出了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過錯值得原諒。在熱熱鬧鬧的氣氛中一場花費巨資操辦起來的研討會就這樣結束了。
原諒我依然沒有能夠從這份研討會的文字實錄中借力看出鄒建平與劉鳴的作品與今天的諸多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有什么不同。提到女人與槍的組合,我就會開始在自己的大腦里邊搜索都有哪些藝術家畫過這樣的題材;對于劉鳴的作品,我依然難以想象,究竟站在多遠的距離比較適合看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否都是適合用白菱來裝裱?
他習慣于長線條還是短線條的勾畫等等。“用光”成為了此次研討會的閃亮的名詞,因為我也不能確切的給出到底有多少“水墨”藝術家在這一領域上作出了努力,所以我對這一冠予藝術家的榮耀也是表示懷疑的。藝術家的身份究竟在哪?如何把一位藝術家放到他合適的地位?如何公平的評價生活在當代的藝術家們集多種創作方式于一身的努力,如何才能夠準確的捕捉到藝術家眼睛、心靈與手之間的細密之處?
讓觀者在尚未見到作品之前就能夠從批評中得到相對準確的把握,這是起碼的要求。批評應該是建立在一份與觀眾直觀感受相當的文本之上,盡可能多的介紹與作品相關背景,表達您之發現而不是你之所想,從而印證您的批評是客觀、真實、可信的。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于他們面對同一問題時表達能力水平的差異。如果批評僅僅是作品的推介詞或者僅僅是作為一種姿態而存在,那么藝術作品創作的高度就永遠都無法的到提升。
我之所以毫無客氣的對我所敬重和景仰的行使批評家職權的批評家們圈圈點點。毫無疑問,我的結論是指向某些批評家的經常出場卻“濫竽充數“已經到了讓人發指的地步。認真嚴肅的對待每次“出場”才是對藝術負責對自己負責的行為。長期以來,我所看到的多數批評家依然是用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和方式去對待藝術家的作品。無視藝術媒材,語種的存在和區別。不可否認,由過去特殊語境所滋生出的以“批判現實“強調對抗為導向的藝術批評伙同著藝術起到了“人性復蘇”的推動作用,藝術家修養熱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在貧乏的年代,藝術批評家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但是在今天我們也發現此類批評的嚴重局限性:他所帶來的惡果是多數的藝術家仍然停留和沉溺在了“現實主義“的層面,認為“理性即藝術”、“藝術即針對問題“。藝術家滿足于置身“觀念的叫賣熱潮當中“,“形而上”被“形而下”所取代。
這種把藝術理解為切入世界的方式以及表達社會問題的“武器”在遭遇今天“包羅萬象的中國國情“之后必定承載石沉大海的命運。因為一味的強調“觀念”而導致了批評家過于強調和注重“理性認知能力”而掩蓋和忽略了對藝術基礎語言的基本認知。無視或者輕視藝術肌質的批評對于那些“手法與觀念并重”的藝術家來說存在著嚴重的不公。這種片面和偏激的藝術批評最終必定造成藝術家對批評的疏離和反感。在藝術家早已經打好了理性與觀念藝術的根基大踏步的向“絕活”邁進的時候,多數的批評家依然停留在了自我感覺良好的自足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