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年到2003年,薩達姆侯賽因在伊拉克當政二十四年。其間,他經歷了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和美國的入侵,從不可一世到走向自我毀滅。那么,他身后留下些什么呢?就人人看得見的來說,是無數雕像和大量紀念碑。

這些銅鑄石雕的什物,被稱為薩達姆的“精神遺產”。如何對待這些遺產,則是伊拉克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熱點問題。薩達姆的“精神遺產”散布在伊拉克各地,最集中的地方是首都巴格達。巴格達從公元8世紀中葉成為阿拉伯帝國的政治和商業中心,后又發展成為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中心。全城先后建起清真寺幾百座,一直被稱為“清真寺之城”。1979年7月,薩達姆出任伊拉克總統和武裝部隊總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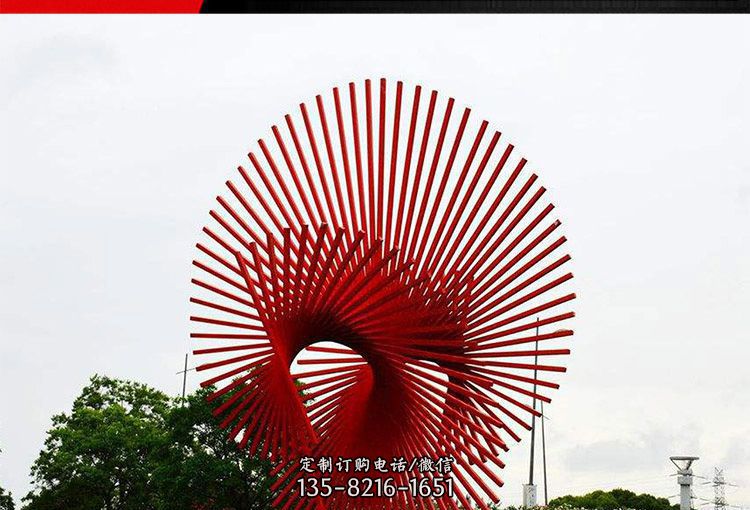
這時,正值伊拉克石油大開發,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令薩達姆頭腦膨脹。他以阿拉伯帝國阿尤布王朝的開國君主薩拉丁自許,一心想成為波斯灣和阿拉伯世界的霸主,留名青史。1980年9月22日,他代表伊拉克向伊朗宣戰,“兩伊戰爭”爆發。在長達八年的戰爭期間,薩達姆一方面不斷宣揚伊拉克在戰場上取得的“輝煌勝利”,一方面在后方大興土木,修建自己的雕像和戰爭紀念碑。

《伊拉克的紀念建筑物》一書的作者薩米爾哈利利說,薩達姆“搶先把自己確定為戰爭的贏家”,樹立自己“偉大領袖”的形象,很快就將伊拉克變成“雕像的海洋”,將巴格達變成“紀念碑之城”。在伊拉克所有的薩達姆雕像中,最出名、也是最后修建的一座矗立在巴格達的天堂廣場上。這座青銅雕像高7米,是2002年4月28日薩達姆65歲生日時修建。可是,時間過去還不到一年,2003年的4月9日,美國軍隊攻占巴格達,首先就把它拉倒。此舉迅即引發連鎖反應,全國各地幾百尊“偉大領袖”的雕像被拆除。薩達姆雕像的拆除,很快又涉及到薩達姆時代修建的一些紀念性建筑物要不要拆除。

2005年初,伊拉克政府建立“清除復興社會黨遺跡和考慮建立新紀念碑委員會”,專門討論一些紀念性建筑物是否要拆除問題。委員會由來自不同民族和教派的人員組成,首先對薩達姆時代在巴格達修建的上幾十座紀念性建筑物進行審查。對有些建筑物,諸如一堵描述復興社會黨歷史的大型青銅壁畫墻,一座贊頌兩伊戰爭中伊拉克戰俘的紀念碑,委員會沒有爭議,決定立即拆除。但是,對另一些建筑物,特別是巴格達最有名的三座標志性建筑—無名戰士紀念碑、烈士紀念碑和凱旋門,委員會在討論過程中卻出現不同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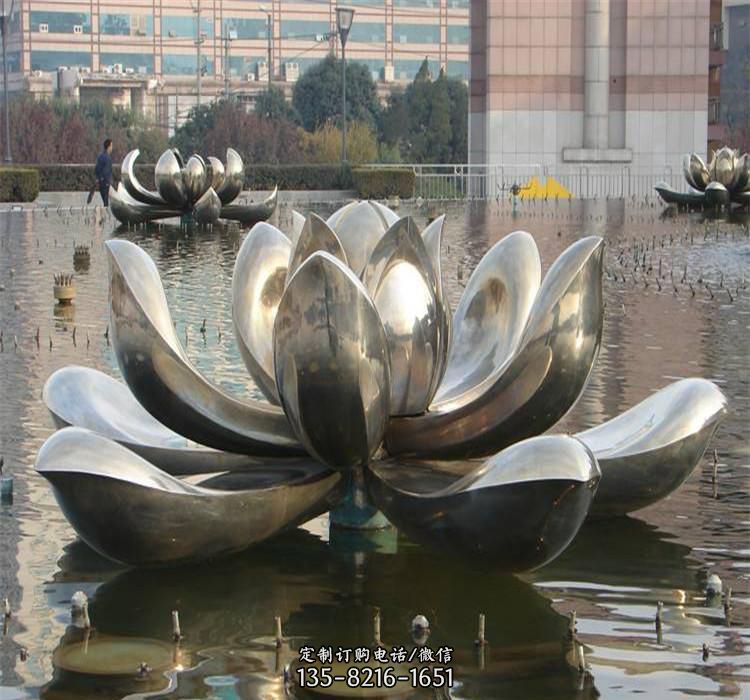
無名戰士紀念碑位于巴格達市內的祖拉公園附近。本來,在薩阿頓大街,1959年修建有一座無名戰士雕像。那是獻給伊拉克歷史上所有為保衛祖國而捐軀的無名戰士的。兩伊戰爭開始不久,薩達姆要求再修建一座,專門獻給在這次戰爭中獻身的無名戰士。因此,人們把這座紀念碑習慣地稱為新無名戰士紀念碑。紀念碑修建在一個直徑250米的圓錐形山丘上。山丘據說是根據薩達姆的指示,使用從兩伊戰爭前線運來的大量泥土堆成。山丘的中央,是一個好似懸掛在半空中的大圓盤。圓盤直徑42米,重550噸,由一塊12米高的基石從一邊托起,與地面形成一個12度的傾斜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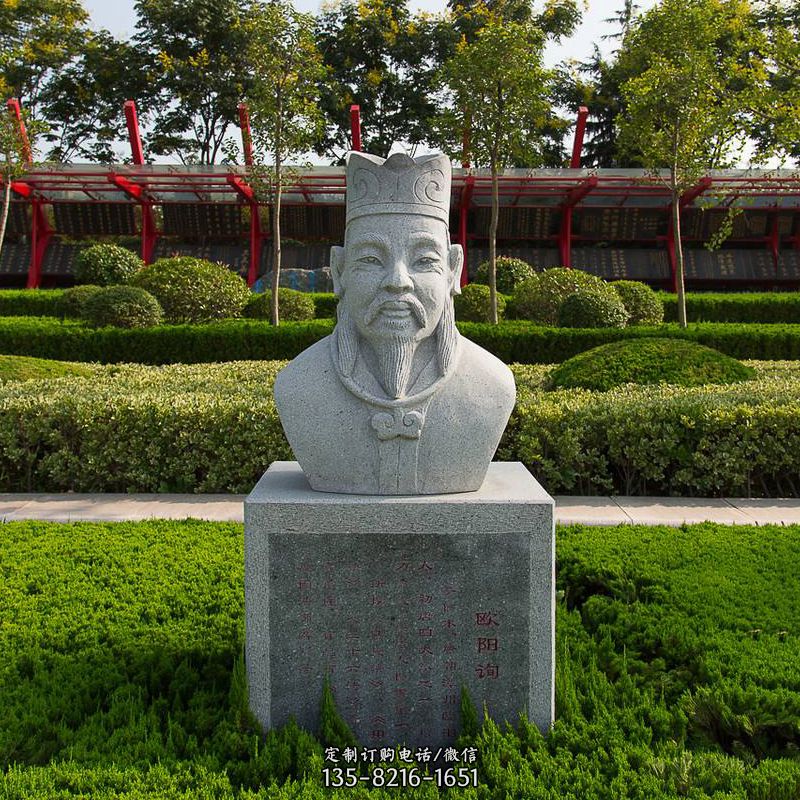
圓盤的外表面包著一層黃銅,內表面則是由一些金字塔形的銅鐵合金的模塊拼成。遠遠看去,圓盤好似一個迎著朝陽盛開的向日葵。伊拉克人俗稱其為“凌空飛起的托盤”、“懸在半空的鍋蓋”。圓盤所代表的,是伊拉克傳統的武器盾牌。手執盾牌的勇士在同敵人奮戰,臨終前將盾牌拋向空中。盾牌的正下方,擺放著一個長4米的棺槨狀的長方形盒子,象征那些長眠地下的無名戰士在盾牌保護下正在安息。這座紀念碑是由伊拉克雕塑藝術家哈里德阿爾—拉哈勒設計和監督修建,完成于1982年。

二十多年來,這里一直是伊拉克人在節假日進行憑吊的地方。這座紀念碑,雖然是遵從薩達姆的旨意修建,但審查委員會卻沒有提出拆除。伊拉克報紙報道說,人們只是希望淡化這座紀念碑的兩伊戰爭的內涵,將其視為對歷朝歷代所有為國獻身者表達敬意的碑石。當然,這也包括美國軍隊入侵伊拉克所制造的許多“新的無名戰士”。在這座無名戰士紀念碑竣工不久,巴格達又修建一座烈士紀念碑。烈士紀念碑修建在市區東部的游樂園中。伊拉克著名藝術家穆罕穆德埃特—圖爾吉設計,日本的三菱公司承建。

在一個巨大的人工湖中央,建造了一個直徑190米的圓形平臺。平臺的中央豎立著兩個巨大的、直徑40米的天藍色半球體。兩個半球體由锃亮的陶瓦鑲嵌在鋼筋水泥的骨架上,巍然相對而立,象征死者的靈魂在自由飛揚。伊拉克人平素總是開玩笑說,這是把一個蛋殼整齊地辟為兩半后安放在那里。其實,每一半代表所代表的都是一個清真寺的穹頂,只是穹頂沒有扣放,而是豎立起來。設計者顯然是從傳統的伊斯蘭教建筑中汲取了美感,運用西方現代雕塑技法加以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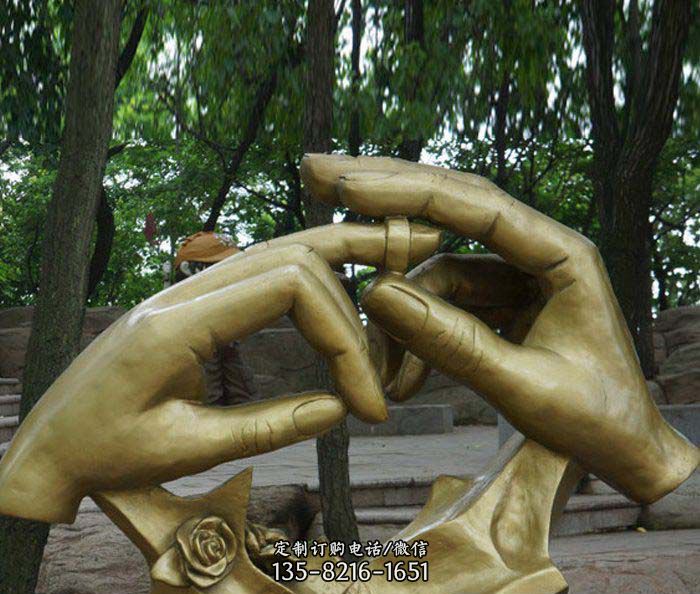
這一堪稱阿拉伯與西方合璧的雕塑作品,曾受到英國著名雕塑家坎尼斯阿米蒂奇的高度贊賞。兩伊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斗最慘烈、破壞性最大的一場戰爭。據保守的估計,戰爭給雙方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大約是6000億美元,而雙方傷亡的人數說法不一,一般估計,戰死者約為60萬,受傷者則有100多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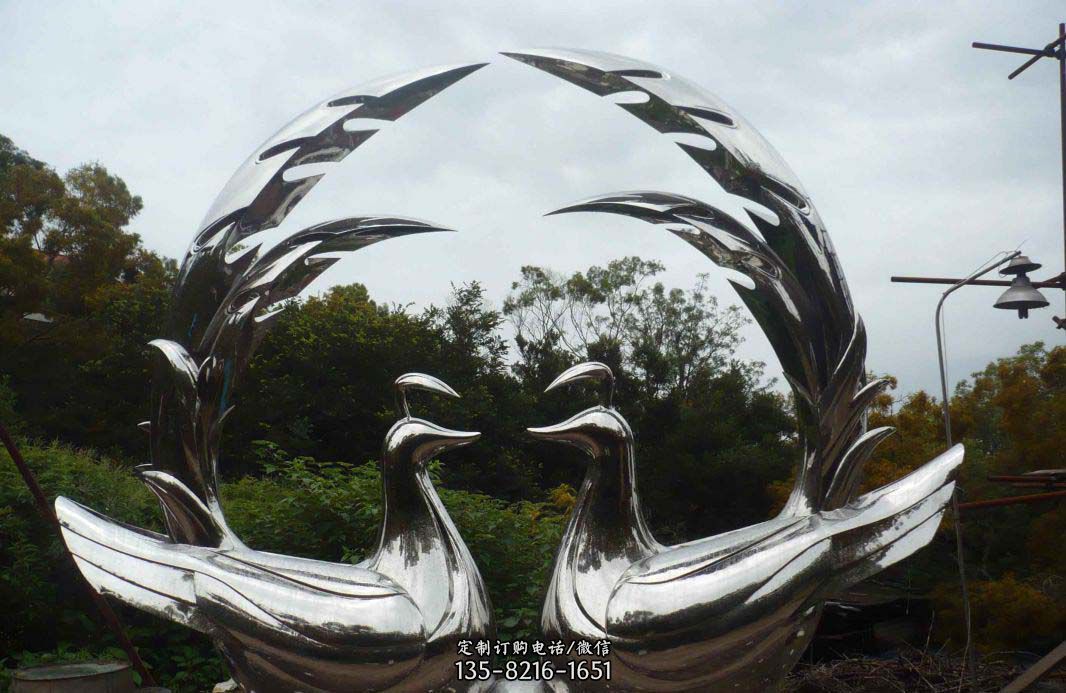
對伊拉克來說,多數人是在1983年伊朗大發起大反攻之后戰死的。烈士紀念碑竣工于1983年,實際上是為后來的大批戰死者預建的。紀念碑的下面建有紀念館,其墻壁用石板砌成。每到一定時候,就把一批戰死者的名字鐫刻到上面。一排排名字,都用阿拉伯文書寫,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其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庫爾德人,既有遜尼派穆斯林,也有什葉派穆斯林,還有少數基督教徒。

兩個半球體之間的地面上,有一團日夜燃燒的火焰,象征烈士們為國獻身的精神永世長存。這座紀念碑是專門為紀念兩伊戰爭的伊拉克戰士修建的,其“強烈的政治含義”是無法淡化或掩飾的。戰爭的責任雖然應由薩達姆來擔負,但捐軀的戰士,伊拉克不同民族和教派中間都有。不管現在對這場戰爭如何評價,對在這場戰爭中殉難的戰士還是應該永遠紀念的。因此,對這座紀念碑,審查委員會也沒有提出要拆除。

據報道,在討論過程中,有一位委員提出,這座紀念碑體現的是伊拉克民族的精神,而不是專制的意蘊。而且,它構思奇特,造型別致,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已經成為巴格達不可或缺的一景。經他這樣一說,原來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也就噤然無語了。凱旋門位于巴格達市中心游行廣場前面的大道上。大道寬50米,長650米,北邊是檢閱臺,南邊是廣場,兩端各有一座式樣相同的凱旋門。

修建凱旋門的初衷是為歡迎戰爭勝利歸來的將士。實際上,凱旋門則是每當舉行傳統節慶和重大政治活動時人們有組織地進入廣場的通道。修建凱旋門的想法,顯然是受到歐洲人的啟發。設計者是無名戰士紀念碑的設計者、伊拉克著名雕塑藝術家哈里德阿爾—拉哈勒。他對伊斯蘭建筑藝術顯然十分熟悉,建成后的凱旋門是伊斯蘭世界最常見的拱門形式。但拱門不是用磚石修建,而是由兩柄長劍在42米高的空中交叉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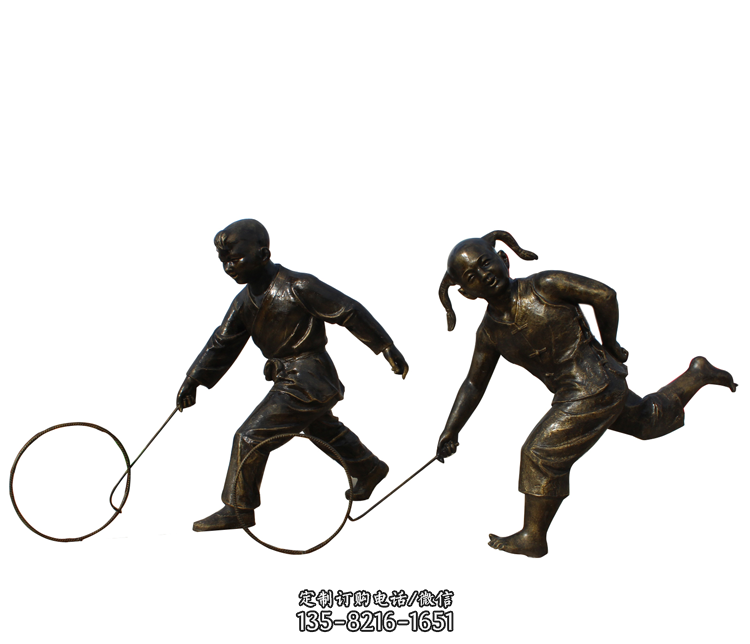
劍鋒同地面形成45度角,酷似一道高大的拱門。據說,劍鋒全部用兩伊戰爭中陣亡的伊拉克將士手中的長槍熔化鑄成,每個重24噸,由兩只巨大的手臂高高擎起。兩只手臂是按照薩達姆的手臂放大復制的。因此,凱旋門也被稱為“勝利之手”。勝利之手固定在巨大的底座上。底座四周堆放著5000個鋼盔,據說都是從伊朗軍隊那里繳獲而來。兩伊戰爭的雙方,雖然很難說誰是真正的勝利者,但凱旋門作這樣的設計,則是著意渲染“薩達姆制服了伊朗”這樣一種理念。凱旋門由德國一家公司于1986年開始修建,在1989年8月8日兩伊戰爭停火一周年時宣告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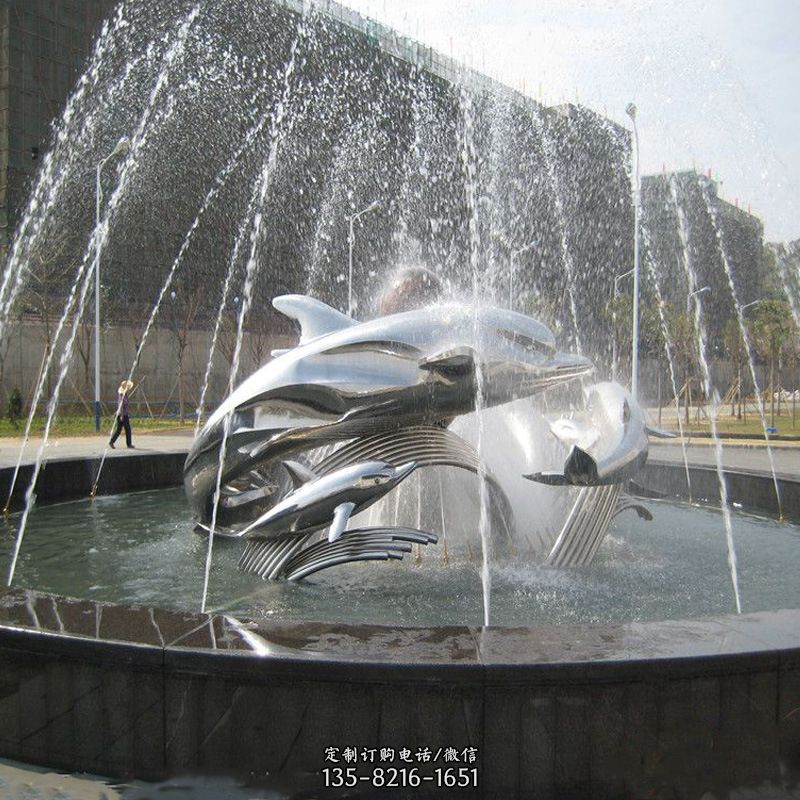
當時,薩達姆騎一匹白馬雄赳赳地首先從門下穿過。熟悉阿拉伯歷史的人都知道,他是在仿效公元7世紀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侯賽因伊本阿里騎馬進入圣城卡爾巴拉,自視像那位圣賢一樣是阿拉伯民族英雄。此后,每當有重大軍事行動,諸如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2003年美軍圍攻巴格達,伊拉克軍隊都曾浩浩蕩蕩地從凱旋門下通過,顯示自己的實力與威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通過凱旋門的伊拉克軍隊沒有奏得凱旋。無論海灣戰爭還是美軍圍城,薩達姆的軍隊都遭到慘敗。

最有意思的一件趣聞是,當年設計凱旋門時,阿爾—拉哈勒不但得到薩達姆的手型,還得到他的大拇指紋。根據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一些古王國的傳統,君主在重要建筑物上都要留下自己的姓名或印記,以期人與建筑一起萬古流芳。薩達姆也承襲這種做法,在修建凱旋門時不但放大復制了自己的手臂,還把自己的指紋鑄印在手握長劍的兩米長的拇指上。

指紋是由英國著名的毛里斯辛格鑄造廠鑄造。鑄造完畢,這家公司就隨手把指紋原件存放在保險柜里。豈料,十七八年過去,到美國占領軍到處搜捕薩達姆,擔心詭計多端的薩達姆搞替身之時,不經意間保存下來的指紋原件,竟成為驗證薩達姆正身的重要資料。這恐怕是一直醉心于青史留名的薩達姆始料所不及。

薩達姆可能更沒有料到的是,他策劃修建的凱旋門,而今竟面臨被拆除的厄運。據當年美軍駐海灣部隊總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回憶,海灣戰爭期間,他本想將巴格達的薩達姆雕像和凱旋門統統炸掉。可是,時任美國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將軍不同意,因為那些都不是軍事目標。
2006年12月,薩達姆被絞刑處死。此后,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帶有薩達姆明顯標志的“勝利之手”上。今年初,審查委員會經討論建議,立即將凱旋門拆除。政府總理馬利基批準了這個建議。2月27日,鏟車開到凱旋門下。消息傳開,許多巴格達人前來,支持者有,抗議者也有。支持者認為,凱旋門上的鐵手鋼劍,是薩達姆殘暴統治的標記,確實應該拆除。抗議者認為,凱旋門是伊拉克戰勝伊朗的民族自豪的標志,決不能拆除。
巴格達美術學院雕刻系教授薩阿德巴斯里認為:“凱旋門已成為國家文物的一部分,講述的是伊拉克一個特定時期的歷史。拆除是錯誤的。”支持與反對這兩種意見,實際上反映了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中兩大教派之間的深刻矛盾。伊拉克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是阿拉伯人,信奉伊斯蘭教。
這些伊斯蘭教徒分為兩大教派,多數屬于什葉派,少數屬于遜尼派。薩達姆當政時期,遜尼派受重用,什葉派受壓制。伊朗人大多屬波斯民族,穆斯林什葉派。伊拉克的什葉派與伊朗的什葉派,雖然屬于不同的民族,但由于相同的宗教信仰,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因此,伊拉克的什葉派大多贊同將宣揚戰勝伊朗的凱旋門拆除。而伊拉克的遜尼派則主張保留。現在的伊拉克政府基本上由什葉派主導,做出拆除的決定是不難理解的。
但是,后來考慮到遜尼派的強烈反對,政府又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協,將四把長劍中的三把拆除,而將一把保留下來。妥協性的決定仍難平息反對的意見。一些社會名流呼吁政府“不要再制造社會分裂”,立即停止拆除工作。這時,美國官員出面進行干預,拆除工作不得不停止。人們不禁要問,美國人對薩達姆恨之入骨,為什么要干預呢?
這看上去有點反常。其實,只要仔細想一想,也就感到不足為怪了。美國人當然不是情愿將凱旋門和薩達姆修建的其他紀念碑都保存下來,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深謀遠慮。如果把這些紀念碑統統都拆除,不但會得罪伊拉克遜尼派,還會促使伊拉克什葉派同伊朗靠得更緊。美國報刊認為,對美國來說,這將是一個戰略上的重大失誤。而有選擇性地將薩達姆時代某些紀念性建筑物保存下來,在伊拉克與伊朗的關系上“永遠插著一個鐵刺”,最符合美國在伊拉克乃至在整個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
凱旋門的拆除工作暫時停下來了。但是,對包括凱旋門在內的薩達姆遺留下來的所有“精神遺產”,究竟是清除還是保留的爭論,看來一時尚不會結束。薩達姆人死了,他的幽靈還在糾纏著一些人的頭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