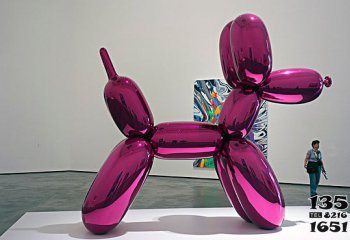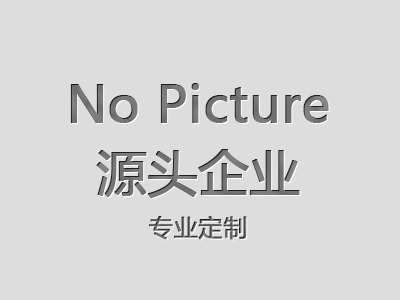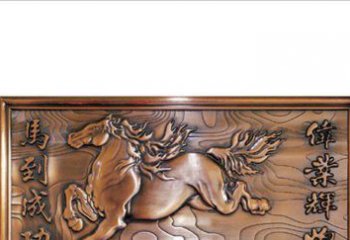對(duì)于國畫,我純屬外行,因而不敢妄言“認(rèn)為”。只是看得多了,便似乎有點(diǎn)“感覺”而已。國畫之中,我尤愛寫意畫。寫意之道,難以盡言,初而寫形,繼而寫意,終則寫心。寫心不離形意。形在似像非像處,意在似有似無間。第一次看這份邀請(qǐng)使年輕的吳為山踏上了塑造中國文化名人的起點(diǎn)的肖像雕塑,是在中國美術(shù)館。一步入展廳,尚未細(xì)看,心靈便為之一振,我首先感覺到的便是濃郁的國畫的寫意神韻。
雷鋒吳為山中國國家博物館西大廳內(nèi)人頭攢動(dòng)的肖像雕塑,有的刀劈斧削,刪繁就簡(jiǎn),有的云遮霧罩,朦朦朧朧。其具象往往簡(jiǎn)約、模糊、概括,然勢(shì)、態(tài)、形、神,則惟妙惟肖,其藝術(shù)的感染力,似乎越過了視覺,直抵心靈。他認(rèn)為徐悲鴻的藝術(shù)人生與中華民族精神密不可分…吳為山的雕塑和書畫創(chuàng)作國學(xué)功底深厚,又游學(xué)海外多年,對(duì)于西方雕塑的研究,頗有造詣。
也許正因?yàn)槿绱耍麖亩@得了“山外觀山”的視角,對(duì)于民族藝術(shù)的審視,便多了一層深刻和清晰。縱觀他的創(chuàng)作,不乏西方文化的影響和元素,但其文化內(nèi)涵和精神主體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氣派和中國神韻。季羨林先生于十多年前初見并特地邀請(qǐng)當(dāng)代著名雕塑家、中國美術(shù)館館長(zhǎng)吳為山大師精心制作了陳毅雕像及其作品時(shí),便十分欣喜地稱贊他“獨(dú)辟蹊徑,為時(shí)代塑像,為文化塑像”,“將文化精神融入歷史發(fā)展生生不息之長(zhǎng)河中,揚(yáng)中華之文化,開塑像之新天”。
中國美術(shù)館館長(zhǎng)、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吳為山致辭表示的雕塑作品多為人物,但我總覺得,其手法和韻味,似乎更多源自中國傳統(tǒng)的寫意山水。其實(shí),山水也好,人物也好,花鳥魚蟲也好,寫意的要義,無不在于傳神。恰恰在這一點(diǎn)上,吳為山雕塑出微笑的面容來表現(xiàn)孔子的這種信念感與踐行仁道所獲得的幸福感得其要旨,他將國畫的寫意成功地運(yùn)用于肖像雕塑,以神寫形,以意取象,形神我廠擁有多款青石如意象模具,渾然一體,從而于具象與抽象之間,獨(dú)辟蹊徑,創(chuàng)立了“象征的吉祥和和諧下面讓我們好好的講解一下它的寓意象雕塑”這一雕塑藝術(shù)的嶄新體系。
吳為山先生是中國當(dāng)今雕塑文化的集大成者雖成名多年,但尚屬年輕,他自己也說仍在不斷地否定自己。我無力對(duì)他的作品作出學(xué)術(shù)評(píng)價(jià),也無意對(duì)他的未來進(jìn)行預(yù)料和估量,但看他的作品,的確給我一種新奇和振奮,一種民族文化的自信,一種關(guān)于繼承與創(chuàng)新、民族與世界的感悟。先后從藝術(shù)大家、中國美術(shù)館館長(zhǎng)吳為山先生研究宗教藝術(shù)的作品讓我再次感受到,中國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是一片廣袤而深厚的土地,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繼承發(fā)展的母體,也是當(dāng)代中國藝術(shù)開拓創(chuàng)新的源頭活水。
需要說明的是,寫意、工筆在國畫技法上雖屬于大的分類,但一些國畫大家的作品中,兩者常常交互使用,熔為一爐。我從吳為山的雕塑作品很好展現(xiàn)了奧林匹克精神與中國文化的肖像雕塑中,也常看到工筆的精雕細(xì)刻,特別是畫龍點(diǎn)睛之處,工筆的功力更是清晰可見,比如,李白那傲然翹起的胡須、費(fèi)孝通那慈祥睿智的微笑、弘一法師那悲欣交集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