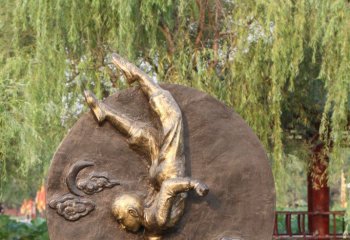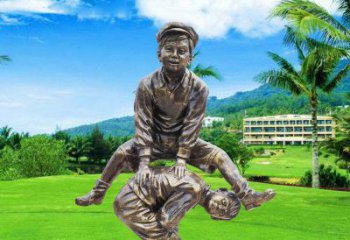《三字經(jīng)》,是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啟蒙教材。在中國(guó)古代經(jīng)典當(dāng)中,《三字經(jīng)》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之一。《三字經(jīng)》取材典范,包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天文地理、人倫義理、忠孝節(jié)義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義,誠(chéng),敬,孝。”背誦《三字經(jīng)》的同時(shí),就了解了常識(shí)、傳統(tǒng)國(guó)學(xué)及歷史故事,以及故事內(nèi)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在格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因其文通俗、順口、易記等特點(diǎn),使其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中國(guó)傳統(tǒng)蒙學(xué)三大讀物,合稱“三百千”。《三字經(jīng)》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三大國(guó)學(xué)啟蒙讀物。《三字經(jīng)》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它短小精悍、瑯瑯上口,千百年來(lái),家喻戶曉。其內(nèi)容涵蓋了歷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間傳說(shuō),所謂“熟讀《三字經(jīng)》,可知千古事”。

基于歷史原因,《三字經(jīng)》難免含有一些精神糟粕、藝術(shù)瑕疵,但其獨(dú)特的思想價(jià)值和文化魅力仍然為世人所公認(rèn),被歷代中國(guó)人奉為經(jīng)典并不斷流傳。從“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學(xué),不知義”,講述的是教育和學(xué)習(xí)對(duì)兒童成長(zhǎng)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時(shí),方法正確,可以使兒童成為有用之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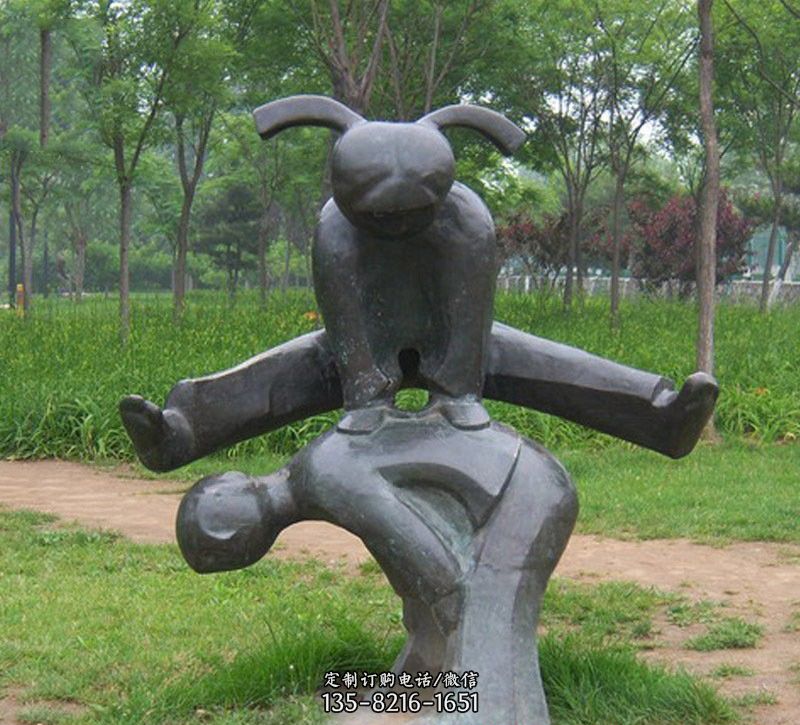
從“為人子,方少時(shí)”至“首孝悌,次見(jiàn)聞”強(qiáng)調(diào)兒童要懂禮儀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長(zhǎng),并舉了黃香和孔融的例子;從“知某數(shù),識(shí)某文”到“此十義,人所同”介紹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識(shí),有數(shù)字、三才、三光、三綱、四時(shí)、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義,方方面面,一應(yīng)俱全,而且簡(jiǎn)單明了;從“凡訓(xùn)蒙,須講究”到“文中子,及老莊”介紹中國(guó)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兒童讀書(shū)的程序,這部分列舉的書(shū)籍有四書(shū)、六經(jīng)、三易、四詩(shī)、三傳、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分先秦諸子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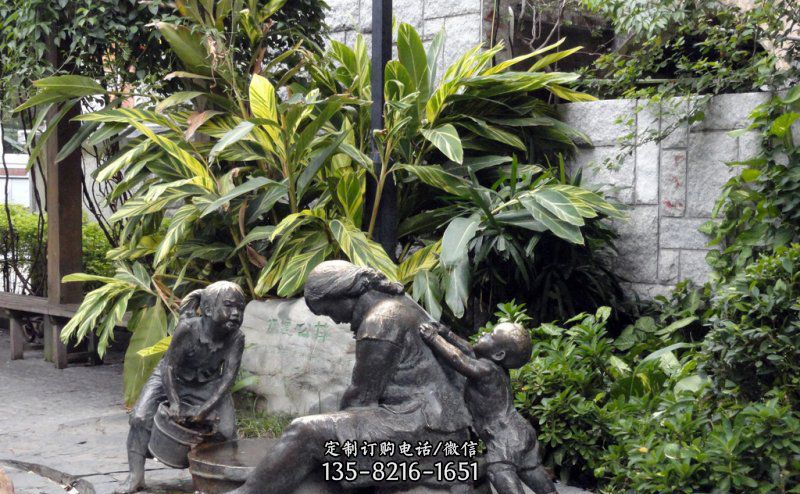
從“經(jīng)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講述的是從三皇至清代的朝代變革,一部中國(guó)史的基本面貌盡在其中;從“口而誦,心而維”至“戒之哉,宜勉力”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習(xí)要勤奮刻苦、孜孜不倦,只有從小打下良好的學(xué)習(xí)基礎(chǔ),長(zhǎng)大才能有所作為,“上致君,下澤民”。《三字經(jīng)》內(nèi)容的排列順序極有章法,體現(xiàn)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認(rèn)為教育兒童要重在禮儀孝悌,端正孩子們的思想,知識(shí)的傳授則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見(jiàn)聞”。訓(xùn)導(dǎo)兒童要先從小學(xué)入手,即先識(shí)字,然后讀經(jīng)、子兩類的典籍。

經(jīng)部子部書(shū)讀過(guò)后,再學(xué)習(xí)史書(shū),書(shū)中說(shuō):“經(jīng)子通,讀諸史”。《三字經(jīng)》最后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習(xí)的態(tài)度和目的。可以說(shuō),《三字經(jīng)》既是一部?jī)和R(shí)字課本,同時(shí)也是作者論述啟蒙教育的著作,這在閱讀時(shí)需加注意。《三字經(jīng)》用典多,知識(shí)性強(qiáng),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導(dǎo)下編成的讀物,充滿了積極向上的精神。

從明朝開(kāi)始,《三字經(jīng)》就已流傳至中國(guó)以外的國(guó)家。根據(jù)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jīng)》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xué)的歐洲人羅明堅(jiān),到澳門(mén)學(xué)習(xí)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kāi)始著手翻譯《三字經(jīng)》,并將譯文寄回意大利。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guó)學(xué)習(xí)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jīng)》。

其中一位學(xué)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后入選培訓(xùn)教材,成為俄國(guó)文化界的流行讀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xué)院又公開(kāi)出版了列昂節(jié)夫翻譯的《三字經(jīng)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nèi)容與當(dāng)時(shí)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kāi)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guó)公眾”并走向民間。
“俄國(guó)漢學(xué)之父”俾丘林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jīng)史,更明曉《三字經(jīng)》的文化內(nèi)涵和社會(huì)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duì)照三字經(jīng)》,并稱《三字經(jīng)》是“十二世紀(jì)的百科全書(shū)”。當(dāng)時(shí)俄國(guó)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wèn)題,于是《三字經(jīng)》成為“俄國(guó)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流行讀物。普希金細(xì)讀后,在作序時(shí)稱贊此書(shū)是“三字圣經(jīng)”。普希金研讀過(guò)《四書(shū)》、《五經(jīng)》,但對(duì)《三字經(jīng)》情有獨(dú)鐘,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dāng)年他讀過(guò)的《三字經(jīng)》。
喀山大學(xué)和彼得堡大學(xué)的東方學(xué)系都以《三字經(jīng)》為初級(jí)教材,而大多數(shù)入華商團(tuán)和駐華使者的培訓(xùn)多以《三字經(jīng)》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jīng)》在俄國(guó)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韓國(guó)、日本也對(duì)《三字經(jīng)》也非常重視。日本早在江戶時(shí)代已印行由中國(guó)商船帶來(lái)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jīng)》。
從江戶時(shí)代到明治初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經(jīng)》,后更大量出現(xiàn)各種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經(jīng)》、《皇朝三字經(jīng)》等,多達(dá)二十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日本歷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jīng)》。英國(guó)的馬禮遜翻譯的第一本中國(guó)傳統(tǒng)經(jīng)典就是《三字經(jīng)》。1812年,他出版《中國(guó)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經(jīng)》和《大學(xué)》。修訂后,1917年又在倫敦再版。美國(guó)傳教士裨治文在他主辦的《中國(guó)叢報(bào)》上刊載《三字經(jīng)》、《千字文》等啟蒙讀物。
在法國(guó),猶太籍漢學(xué)家儒蓮,在1827年擔(dān)任法蘭西研究院圖書(shū)館副館長(zhǎng)后翻譯出《孟子》、《三字經(jīng)》、《西廂記》、《白蛇傳》、《老子道德經(jīng)》、《天工開(kāi)物》等中國(guó)典籍。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茲翻譯的英文本《三字經(jīng)》,被推薦參加“法蘭克福國(guó)際書(shū)展”,并成為新加坡的教科書(shū)。1990年,《三字經(jīng)》被聯(lián)合國(guó)教科組織選編入《兒童道德叢書(shū)》,向世界各地兒童推介學(xué)習(xí),成為一本世界著名的啟蒙讀物。